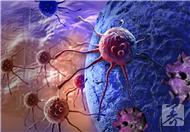尽管拥有了总数超过一百万美元的资产,身为技术主管的保罗·马还是担心自己未来的财政问题。“我们大概是所有美国家庭中最富有的那1%……所以我没什么可抱怨的,”他告诉我,“但是我还是不觉得我很有钱。”只有积累了数百万财产才能让他彻底放松。
劳拉·德尔加多是一个带着三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工作是出纳员。一分存款也没有的她,在许多方面倒不是太关心。跟马先生不一样,她没有那么多奢望。“一无所有不总是坏事。”她说,提醒自己,事情总是会更糟。为了适应她的困境,劳拉只把花销限定在最基本的衣食住行上,并过滤掉坏消息,始终看到事情光明的一面。这种做法可以让她不那么忧虑了。
在新书《停止漂泊:家庭的危机时刻》中,我与不同经济条件的家庭接触之后才知道,富人不认为他们得到的已经足够了,努力想要获得更多;而中产和工薪阶层的家庭意识到,他们再怎么做,也只能有限地改善他们的处境,所以他们只能降低预期,并尝试去适应更简单的生活。这些管控危机的不同方法不只是反映了不平等,它们实际上在消除这种不平等。
这就是感性的故事,隐藏在数据反映的事实背后——我们生活在朝不保夕的时代。这个故事多少都被谈及,或者被验证。它是向我们——所有在这个不平等和不安全的时代生活的人——收费。当美国人争相保住工作,努力对抗减薪,负担不断上升的学费,投资退休基金,管理债务,拿出紧急医疗的费用和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里给孩子增加一点优势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有了深层次的心理反应。
当然,针对不同人群,这些反应的表现和感觉也是不同的。随着经济不安全感增加了,我们国家贫富之间的鸿沟也加大了。这意味着,不同的家庭面临不同的障碍,也可以处置不同数量的资源。但是,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是担忧忧虑。从衣食无忧的企业高管,到收入较低的零售业者,每个跟我谈过话的人都被类似的东西拖累。不管什么阶层什么收入水平,大家都觉得没有安全感。我们只是处理方式不同而已。
像劳拉·德尔加多一样,许多我交谈过的中产和工薪阶层家庭,已经被打压得如此了——他们已经放弃梦想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相反,他们试着去忍受可能面临的更多的不安全感。例如,当劳拉的暖气因为欠费而被停掉,她告诉我,“就当和孩子一起露营”。
与此相反,富裕的家庭走向相反的方向。他们不逼着自己适应更大的不安全因素,而是试图建立一个可以保护家人的经济防火墙。对于一些我交谈过的富裕家庭,他们想要在北部花一千万美元置办身家,才觉得自己在经济上完全有保障,能使家庭有资源来渡过遇到的任何危机。有了这样大的挣钱目标,许多富裕家庭担心他们会挣不够钱。
经济条件往往是旁观者清。但在现实中,经济条件会在内心深处影响着我们的想法和感受。在这个每个人都要单打独斗对抗不安全因素的时代,我们想出了应对策略——一些思考和感觉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处理不平等性质的变化和生活在这个时代可能遭遇的风险。
和经济差异一样,情感差异也有真正的后果。我们我们为个体分开的代价,是不平等和不安全的经历往往和个人问题——一些我们需要比社会问题更优先解决的东西——一起出现。富人想要的更多,其他人习惯于越来越简单的生活,那么不平等就会恶化。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一摊事,我们就无法团结起来阻止这种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