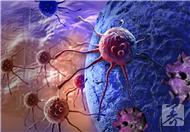“你信教吗?”
我困惑地皱了皱眉。我只是告诉这个家族朋友,一个退休的牙科医生,我患有发作性嗜睡病。他真的在问我关于宗教的事么?
“我想我相信精神的力量,但不信教。”我结结巴巴地说。
“你祈祷吗?”
“不……”
“看,这就是问题,”他很有热情去解答,“你需要的只是内心的平静,你需要和上帝接触以求得内心的平静。”
我的眼睛看到地下,想搜索词语去回复,但我很快意识到,我并不同意他的说法。
当我告诉别人我有发作性嗜睡病的时候,经常听到这样的问题:“你试过瑜伽吗?”“试一下维生素C怎么样?”还有“你祈祷吗?”
人们总是处于善意地给出解决方案。我明白。当然,多少让人沮丧,当别人得知你的病情时,他们首先想到的时候你没有意识到的解决方案,就算我已经病了很多年了。但是,这仍然可以原谅。
但是最困扰我的是,当我告知他们我有发作性嗜睡病的时候,他们就认为我是在寻找解决方法。
让我澄清一下:我,朱莉·弗吕加勒,并不是想在发作性嗜睡病中被拯救出来。
发作性嗜睡病是一种睡眠/唤醒周期紊乱的神经疾病,全球范围内,每两千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患有这种病。每天我都睡很多。当我笑的时候,我的膝盖有时会弯曲或我全身崩溃这种,麻痹症状称为猝倒。此外,还有可怕的幻觉环绕我的睡眠。
然而,突发的嗜睡只是我的一部分,就像我头发的颜色和遗传的特征。我为我自己是一个发作性嗜睡病患者而感到骄傲。自从被诊断出这个病,我跑完了波士顿马拉松,成为全国的发言人,创立了一个公益性机构,并出版了一本自传。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在我一生中可以做成这么多事情,而且在我20多岁的时候。
我不是一个奇迹女孩,远远不够。发作性嗜睡病在日常中挑战我。我白天吃两次药,晚上也吃两次药,吃药会带来不怎么愉快的副作用。现在我依然会每天收到睡眠攻击并猝倒。在处理完繁琐的保险事务和和一个傲慢的药剂师打交道之后,我在药房的停车场大哭一场。阻碍总是不断产生。
但对我来说,这个病并不能分成好的或者邪恶的。有时它会是一种强烈的挫败感,其他时候会是无限的激情和动力的源泉。现在我不再从不适中逃离,而选择静静地站着,看着它们潮起潮落,
在你同情我或者给我出解决方法之前,考虑一下,你的担忧并不见得是我的担忧。你对我的疾病的感觉或许跟我的不一样。
我很乐于情况得到改善,尝试改变很多的生活方式的和接受不同的治疗。
我相信一个强大的身心连接,尤其是当它涉及到免疫系统。
但是我也相信人体是复杂,超出现代医学和替代疗法之外。
简而言之,有些事情并不容易可以解决的。
如果有人有蛀齿,他可以通过祈祷把蛀齿去掉吗?如果有人摔断了手臂,瑜伽可以修复伤处吗?有趣的是,嗜睡症的人失踪的90 -
95的神经元都在大脑中调节睡眠和清醒的界限之间。虽然这些神经元肉眼看不到,但是真的。
坚持简单的解决办法,我的经验感觉是无效——就像嗜睡症好像是在我的控制之下,或者是我的错。这让我感到羞愧和内疚。要是我锻炼得更多……要是我没有压力…如果我更健康…
羞愧比任何疾病都严重。内疚比任何疾病要痛苦。在我看来,我们的文化过于强调寻找快速的解决方法和避免不适,而不是在挑战中学习和观察。我们忘记了困难也是人生的一部分,瑜伽、改变饮食、祈祷和药物都不能让我们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