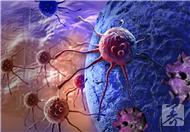距离得到最初的诊断已经过去十年了。我开通了第一个赫芬顿邮报博客,去年我一直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以及倾听其他人的故事。我最惊讶的是很多人仍在使用精神类药物。这些不当的药使我住进医院里,它也能帮助我们找到自己正确的诊断并最终找到治疗的办法。
我度过了我大学的第一年,但我知道有些事情出了差错。我封闭自己与现实脱节,我的成绩很糟糕,我没有和其他人交流,而且我总是有可怕的想法。我的一个治疗师在长岛,但我无法到达那里,我几乎不能把思想集中在一起。他希望夏天赶快结束然后他就能把我托付给城市里的一个心理医生,但我想要的答案,而不是毒品。
这并不是说我怀疑药物的疗效。我质疑药物对道德和精神的影响。在外面,我不想显得软弱。独处时,我想象一个最佳的,最真实的“自我”我的意思是,药物会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点。虽然自称寻求救济,我却不得不在失落中成长。我受到乏味生活的折磨。我的神经已经成为一个确定的因素,大脑中的化学物质可能是非个人的,但它就像一个魔法药水,催生了我们自己,并改变它,就像死亡或更糟。这里没有自我,不论是我们身体还是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识。
我不得不选择一种属于科学类的书。我一直在研究我的意识和我的生活,现在是时候来了解我的大脑了。尽管我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触摸自己,但是我想更进一步去了解。我可以培养和改变自己的意识,用决定和习惯来代替药物对大脑的控制。
我的第一个医生诊断我得了抑郁症之后我开始写书。我的精神状态发生了改变,但没有达到最好的状态。我优柔寡断的性格转变成了粗心遗忘,我很少对事情做出反应。我不再去上课,而是把时间用来睡觉。当我向我的医生说这些症状的时候,他只是加大了药的剂量。最后我成为了一个狂躁的失眠的人。我的大脑就像被火烧了一样,我的身体想要逃离,有巨大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响着。
医院诊断我具有精神病特征的情感障碍。但我知道我不是精神分裂症。我的听觉幻觉是不适当的药物治疗引起的,我使用了低剂量的抗抑郁和心境稳定剂。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呕吐和昏睡症状减轻。我的思绪的速度开始放缓,我可以控制我的情绪,恐惧慢慢消退,我开始重新进入生活。我不再担心,开始做我自己。不再关心什么是双相情感障碍,这不仅仅是情绪的变化。
我的一些朋友吹嘘他们每天睡很少的时间,如果剥夺自己睡觉的能力完全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也许没有精神分裂后我可以生存下去,但我能够从大学毕业吗?做完并交出资金及的第一份考卷?我不只是想生存下去,我更想要好好地活下去。十年后,我实现了目标,我把药维持在原剂量的一半水平。“我有责任和信仰去创造自己想要生活,并开始真正的自我。